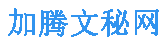纵览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屏幕,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可谓蔚为大观,占领了电视剧市场的大半江山,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成就虽然有目共睹,却也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在“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语境中重温革命的理想、继承革命的价值并将其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精神资源?如何进行叙事范型的创新,从而更具技巧性地讲述革命故事,用更好的形式承载革命的内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创者们如果想要推陈出新,就必须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近播映的《十送红军》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突破与创新之作,也在创作实践上回应了上述问题。该剧是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献礼剧,该剧导演毛卫宁、编剧李修文为观众重现了长征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穿插讲述了十位普通红军战士的生命故事。“他们不同年龄、性别、兵种,却有着共同愿望,那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和传递红色的星星火种。在这群默默无闻的战士的共同守护下,红色政权的火种终于安全的保留了下来,渐成燎原之势。”[1]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从2014年6月11日开播至7月15日收官,电视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持续走高,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该剧的热播也促使我们探究其背后成功的原因。
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险,也是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正因为此,表现此段历史的影视剧数量很多。在既往的电视剧作品中,多将视角聚焦在领袖人物身上,正面描写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政治韬略和革命实践,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就是电视剧《长征》(2001)。《十送红军》则改变了之前的关注重心,将视线下移,聚焦在长征途中的普通战士身上,书写他们在战争中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同一个长征故事被不同的叙述者叙述的时候所呈现出的不同的面向。《十送红军》的特色正在于它用全新的平民立场重述了革命故事,从而让革命的普通战士从历史的背景走向前台,站立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十送红军》是“无名战士的赞美诗”[2],该剧告诉我们:“史诗性”不仅体现在伟大的“有名英雄”身上,更体现在牺牲在革命中的无名英雄身上。每一个普通人在革命中都是英雄,都值得被纪念和被讲述。
《十送红军》是关于十个战士的故事,也是主创者们为我们雕刻的长征群像。与以往长征故事用大篇幅集中塑造几个核心人物不同,该剧以“单元剧”的形式,用十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接力来表现长征。如果说以往的故事是以长篇小说的方式来讲述,那么《十送红军》就是以短篇小说连缀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该剧同时又是十个短剧。正因为此,《十送红军》其实是一部超浓缩的电视剧:每个故事的情节都很紧凑,节奏也非常快,因此具有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无疑能最大程度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投入故事之中。
《十送红军》的情节构思巧妙且充满传奇色彩。例如,第五个故事里孤身寻找队伍的女红军戴澜,她女扮男装混入敌营的冒险就颇具当代花木兰的意味。第八个故事里的小战士邓秋生乙冒名顶替和自己同名的“长胜模范”邓秋生甲,在巧合与误会中演绎了“名字的谜题”。第九个故事是战士贾学会带着一班战士奉命护送参加红军的农家少年郭小满的尸体回家,这个故事把情节的曲折和战争的残酷结合在一起。而第四个故事炊事员贺老憨和红军战士郑十一斤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如同父子般的革命友谊也在战火中得到了升华。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产品,情节必须是“吸睛”的,才能让观众“看得下去”。从上述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李修文对情节的掌控能力。
情节的出彩固然是首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用立体生动、充满个性的人物来打动观众。在《十送红军》中,主创者为我们塑造了十个平民英雄,他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演绎着不同的生命史,以坚定的信仰为长征做出个体的牺牲,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十送红军》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神枪手张二光的成长经历。他在“神枪手连”遇到一群颓废的老兵,这群人枪法精准,却因各种原因变得一事无成。在他和这群老兵之间,产生了各种具有喜剧性的戏剧冲突。他试图鼓励老兵们重振对生活的信心,却意外地失去了开枪的手指。于是,故事发生逆转,老兵们反过来鼓励他。最终,他们都找回了自我,一起参加湘江血战,最后壮烈牺牲[3]。在这个故事中,张二光的成长与其说是“想成为神枪手”的故事,还不如说是“想成为神枪手而不能”的故事。正是因为这种“不能”,革命中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个体的光辉被磨砺出来,张二光完成了一个战士的蜕变。
“十次感动,十次别离。”《十送红军》之所以让人感动,是由于对情感的出色表现。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被还原到最粗粝的状态,这反倒让我们剥离了平日里种种附加在个体身上的东西,显露出人性的本真。这种情感可以是小爱:亲情、友情、爱情,也是大爱:为革命理想、为国家民族、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无论是小爱还是大爱,这些情感的浓度和烈度都是当下生活所不具备的,构成了当下生活的对照。不管是“小爱”的真诚、质朴与纯洁,还是“大爱”的伟大、光明和崇高,都是我们早已久违了的精神气质,也为当下萎靡而浮躁的精神生态提供了一份历史的参照。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个父亲寻子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军团长下达命令,要求父亲钟石发必须从四个参加敢死队的儿子中带回一个,到相对安全的中央纵队,为钟家留一个后。于是,钟石发开始了寻子的旅程,但这趟旅程并不顺利,他不仅没有把任何一个儿子找回来,反而亲历了几个儿子的牺牲。但在此过程中,父子之间的心防被解开了,父子之间的隔膜被打破了,他们终于获得了彼此的宽宥和原谅。这是一个惨烈的告别,钟石发和他的儿子们都牺牲了,但“寻子”的过程却是一个重新获得亲情的故事。枪林弹雨之中,家人的羁绊和家族之爱反而更加浓烈地体现出来,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主角和配角都出彩的故事――这是该剧在叙事上最大的成功。我们早已知晓,父子之间那种爱恨交缠的关系是十分难以表现的,但《十送红军》不仅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父子关系,体现出不同的矛盾和和解,同时还具有不同的差异和层次,彼此之间构成镜像关系。在这个故事中,编剧精致的叙事安排和演员的出色表演相得益彰,从细节出发铺陈出一个异常感人的父子故事。
时代狂飙、革命理想与改变世界,这是史诗时代的宏大叙事,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面对这些抽象的“宏大”,《十送红军》更注重把宏大具体落实在“日常”层面。他不仅采取了平民立场叙事、描绘平民肖像、抒发平民情感,还注意描绘平民市井的日常生活、倾听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革命的“兹事体大”,被表征为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饭,被转化成世俗生活的诗意瞬间。虽然《十送红军》的节奏很快、浓度很大,但在这种快速推进的情节逻辑线中,我们依然注意到很多细节的刻画和情境的描摹:例如钟石发故事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父亲背儿子”的意象,以及在最后战役打响的前夜,钟石发和钟二发在树林里呼喊兄弟几个名字的画面。这些看似旁枝逸出的闲笔,其实是时间的褶皱,在快节奏的戏剧性和慢节奏的抒情性之间得到了叙事的平衡。
二
除了“讲什么”,还有“怎么讲”。正如前述,《十送红军》在叙事上的突破在于用十个故事组成拼图来构造“长征”的整体。但是,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端是单元过于独立而故事的整体性缺失。《十送红军》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用“穿插”的方式来进行整合。编剧李修文将十个故事镶嵌在长征路上,由此看似横向的板块叙事有了纵向的时间线索。对于整个故事的框架来说,这是一个发生在长征路途上不同地点的故事,从瑞金到延安,整个故事是“移步换景”的,故事的接力也是长征的接力。十个故事固然各有自己的主人翁,然而这看似封闭圆满的结构却被某种人物关系的联结所打破,变成一个半开放的故事。于是,一个关于“长征”的叙事网络被编织完成。以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的过渡为例:第一个故事是主角钟石发寻找四个儿子,而在这个段落中,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张二光也作为配角出现了。在此故事结尾处,为掩护大部队撤退,钟石发和钟二发父子与张二光并肩战斗,最终父子战死沙场,张二光带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地契突出重围,于是故事自然过渡到张二光的身上。回看《十送红军》,如果我们细加揣摩,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叙事是具有难度的,处处用心而不留痕迹,无一处不体现出编剧的匠心。
在几篇关于该剧创作的采访中,编剧李修文都提及了“向美剧学习”的想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需要向美剧学习?这是后现代的拼凑和混搭吗?最后的成果会不会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这一说法无疑会产生大量的质疑。不过,《十送红军》的成品似乎驱散了我们的疑惑,这一看似混搭的“革命+美剧”不仅没有影响革命主题的表达,反而以更加多元的叙事技巧呈现出革命主题。这是一个精神内核和叙事外壳的关系。对于“主旋律”影视剧而言,大众总是有太多的抱怨要吐槽,诸如说教、死板、机械――最为人诟病的是故事不吸引人,“看不下去”。而美剧的叙事技巧无疑起到了“盘活”故事的作用。好莱坞和美剧有丰富的影像叙事经验,如果中国的影视剧用开放的视野和兼容并包的创作态度来平行借鉴美剧,不仅不会损伤中国故事的表达,还会在技术上升华和加持叙事的戏剧性。
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十送红军》的影像所呈现出的纪实风格。当我们看惯了诸如“抗日神剧”中手撕鬼子之类的诡异情节时,这种“真实”无疑是难得的体验。在高清摄像机的捕捉下,战争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一面被展现出来。在剧中,我们看到被轰炸过的城市、化为碎片的房屋、血肉模糊的身体、满是灰尘的面孔……这些画面具有电影般的氛围、油画般的质感,也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也不禁为之心惊胆寒。面临着如此真实的战争,个体还能保持对革命的理想,这也使我们重新体验到史诗时代信仰的能量。
三
毫无疑问,“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这一命名的内部具有某种悖论结构: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是表述革命正确性和政权合法性的“历史叙述”,必须体现“主旋律”的意识形态诉求;另一方面,电视剧是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产品,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和商业诉求。这就使该类型电视剧的主创者们面临着双重的困境:如果过于“文以载道”,就会变成宣扬革命历史的教科书,使电视剧成为政治的背书;如果过于“市场化”,就会掏空革命精神,使革命变得题材化、娱乐化、媚俗化。因此,较之其他类型的电视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更具有挑战性,需要更大的叙事智慧和创作勇气。不过,恰如有论者言及的,《十送红军》是一部“表现主旋律又不失市场化的作品”。[4]《十送红军》在“告别革命”、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时代带领我们重温了革命的精神遗产,也以出色的叙事技巧重构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内部范型,在革命精神与大众文化之间保持了张力和平衡。《十送红军》的实验,为我们讲好革命故事和“中国故事”[5]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个案。
在某种意义上,《十送红军》也在2014年这一红军长征80周年纪念中重新提醒了我们“长征”的意义所在。学者汪晖认为,“短20世纪”是围绕革命的主题展开的,是“漫长的19世纪”异质的他者,两者构成了一组对位关系。20世纪的90年代则与“漫长的19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性,“‘90 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6]而在我看来,站在2014年的时间节点上往回看,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正好处在90年代的延长线上,并没有超越90年代所开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态,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漫长的90年代”(或者放在更“长时段”的视野看,我们的21世纪前两个十年也是“漫长的19世纪”的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90年代”,“革命”的乌托邦被无情地放逐了,世界变成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平坦世界”[7],任何超越性的价值、任何“另一种想象”的可能性都消失殆尽。但历史的幽灵从来不会消失,它只会隐藏在当代日常生活的背后,衍生、回旋、延异。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重走长征路,或者仅仅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重温80年前那场艰苦卓越的旅行才具有格外的意义:这是重新思考“短20世纪”遗产的方式,是“观看的政治”与“微观的反抗”,也是一种想象中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询唤”。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俗时代再次听见《十送红军》[8]淳朴而悠扬的歌声,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十送红军》不仅是穿越时代的金曲,更是共和国的公共记忆。它的弦歌不绝正好告知我们,“革命”之于中国,既是文化记忆,也是情感政治。电视剧《十送红军》开创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新的叙事模式和表意实践,不仅为长征的历史增添了一份新的阐释,也通过折返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对当下理想匮乏的精神生态的关切。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光影的流转中重温了革命时代的理想、热血和情怀,这或许才是《十送红军》主创者们最念兹在兹的东西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1]央视网电视剧频道对该剧的“剧情简介”,http://dianshiju.cntv.cn/special/sshj/。
[2]《武汉作家李修文任编剧 〈十送红军〉将登陆央视》:http://hb.sina.com.cn/view/yc/2014- 06-09/09181 734 91.html。
[3]故事的复述参照《〈十送红军〉的十个故事》,http://dianshiju.cntv.cn/2014/05/19/ARTI14 00466909875 102_2.shtml。
[4]《〈十送红军〉7月15日收官 十次别离感动荧屏》,http://dianshiju.cntv.cn/2014/07/15/ART I1405390202021 102.shtml
[5]参见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载《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范潦閫沸轮榈?008年版,第2页。
[7]此一表述参见(美)大卫€饭踔竞搿⑿焯α嵋耄骸跺居钪饕逵胱杂傻乩怼罚貉С霭嫔?014年版。
[8]1961年8月1日在北京音乐堂首演说明书《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发表了《十送红军》。由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根据江西赣南民歌《长歌》改编。《十送红军》的歌词借叙事来表达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热烈期盼。